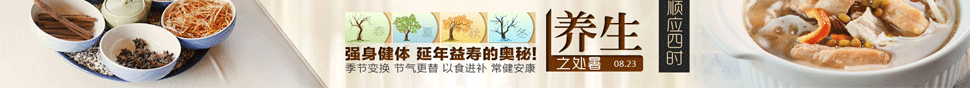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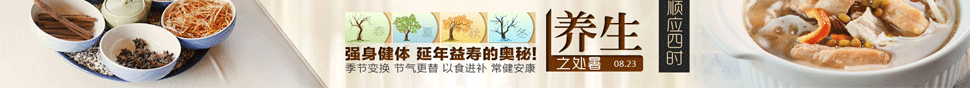
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
作者
卞毓方
一
“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倘若现在有谁提问,相信您多半会说出正确答案。但在三十六年前,在毛泽东七十二华诞的宴席上,当伟大领袖搁下酒杯,盯住来自盐城的知青代表董加耕,笑吟吟地发问。董加耕顿时张皇失措,如坠五里雾中。
“盐城有二桥?”他一开始就把“乔”听成了“桥”,盐城的桥很多,主席为什么单问二桥?是不是他老人家到过盐城,走过那两座桥?还是那两座桥特别有名,都传到主席耳里?盐城的大桥小桥长桥短桥老桥新桥在董加耕的脑海里急速打架,奈何场面隆重,众目睽睽,由不得他细想,董加耕于是硬着头皮,放胆应对:“西门登瀛桥,东门朝阳桥。”
“哈哈,我说的是人,不是桥。”毛泽东这里再次展示了他借古喻今、涉典成趣的艺术魅力。但见他环视左右,掰着手指头解释:“盐城‘二乔’,一个是胡乔木,一个是乔冠华。”
此事发生在年12月26日,地点在中南海;“盐城二乔”的美谈由是飞出餐桌,飞出京城,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胡乔木(年6月1日--年9月28日)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祖籍盐城鞍湖乡张本庄,年生,扬州中学毕业,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肄业。年奔赴延安,改名“乔木”。改名是当时革命青年的风尚,以示告别旧我,焕然一新。“乔木”这名儿,显然是受了《诗经·伐木》篇的启示:“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乔,形容高大,乔木,就是高耸、挺拔的大树。号角在前。光明在前。大时代在前。延安的红色青年,谁不希望自己成为一株拔地擎天的大树!乔木不仅自己全身心向往,还动员妻子李桂英改名“谷羽”。你有没有悟出其中的奥妙?“谷”,就是山谷,“羽”,就是鸟,鸟儿从深谷飞出,一翅落在高枝上——不正象征着嫁给了乔木吗!
乔冠华(年3月28日-年9月22日)
乔冠华,祖籍盐城庆丰乡东乔庄,年生。先后毕业于清华大学和德国杜宾根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年在香港参与创办《时事晚报》,负责撰写国际时评。他的评论,既目光如炬,洞中肯綮(qìng),又文气淋漓,感性十足,一时哄传港岛。有同事梁先生出主意,说:这么好的文章,只发《时事晚报》一家,太可惜了。你不如换个笔名,通过中国新闻社发往南洋,供华侨报纸刊用;笔名,可以就叫“乔木”。借助中国新闻社,一稿多发,尽量扩大影响,乔冠华自然乐得赞成;至于笔名,他觉得自己姓乔,又长得身高体瘦,活像一株乔木——难得梁先生考虑如此周密——也便一并笑纳。
从此,中国有了两位“乔木”。都是盐城人,都念过清华大学,都在共产党内,又都擅长写理论文章;世人为了分辨,通常称他俩为北乔和南乔。
国际述评集-(乔冠华著·重庆年版·《新华日报》文选)
年,南北二乔在重庆碰到一起。前者是重庆《新华日报》的编委,后者是赴渝参加国共谈判的毛泽东的随员。两位乔木都是才子,都是大手笔,日常难免混淆不清。尤其当他俩在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更让人有“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之叹。于是,有人提出请他俩中的一人更名。更名?更改一个业已为社会普遍仰视,并且日益发出强光烈焰的大名?让谁谁都不干。南乔说自己的列祖列宗就姓乔,而且身高一米八三,站在哪儿都像一棵树,乔木一名自是非他莫属。北乔说自己“注册”在先,早在年,他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文学评论,署的就是“乔木”;何况连老婆谷羽的名字,含的也是同一典故。双方各以全力“对掌”,寸步不让。事情惊动毛泽东,于是就生发出毛公为二人“断名”的佳话。
年8月,胡乔木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左起:张治中、毛泽东、赫尔利、周恩来、王若飞、胡乔木、陈龙。
关于这件事的时间、地点,版本不一,有说是在当日的重庆,有说是在建国后的北京。据叶永烈考证,应以重庆为正确。大致经过是:有次聚会,适逢毛公和二乔都在座,两人重名的事儿,又被在一旁的好事者提了出来。毛公仰脸问南乔,你原来叫什么名字?南乔回答说“原来叫冠华”。毛公听罢,双眸一亮,拊掌道:冠华,冠华,这名字很好嘛!你以后仍叫乔冠华,名字既响,又不改姓。这边敲定,那边就好办了。毛公转脸向北乔,说:你可以保留“乔木”,但你原来姓胡,要加上姓,叫胡乔木。
一团死结,在毛泽东手里迎刃而解。
名字这玩艺儿,有时仿佛通灵。从历史的角度看,北乔长期担任毛泽东的秘书,就像背靠一株参天蔽日的大树,说他“出自幽谷,迁于乔木”,颇为形象、传神。而南乔,虽然也官运亨通,一路做到外交部长的高位,但他与最高领袖之间,毕竟隔了一段距离,就仿佛鸟儿在高空盘旋,始终没能歇羽巨柯繁枝。不过,弃“乔木”而取“冠华”,倒是名至实归,冠华,冠华,他在新闻和外交领域的建树,不管后人如何评说,也堪称是“名冠中华”。
二
盐城市盐都区鞍湖镇张本村胡乔木故居
去乔木老家的路上,雪已经化为泥浆。罕见的大雪,在这苏北地带,仿佛是突然而至,从昨天下午就一个劲地飘洒。那会儿我刚刚抵达盐城,心禁不住一颠一颤。我怕,怕大雪封了道路。为了这次采访,已煞费苦心地作了多日准备,惟恐到了跟前,又被雪神的银杖阻拦。这担心不是没来由的,昨天傍晚看罢新四军纪念馆,乘坐的新款“奥迪”就是以乌龟的姿态,一步一步地挪回宾馆。可以想象一夜雪紧,再狠狠地一冻,明天城外的乡间小路会是一番什么光景。夜间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踏实。连梦也在忐忐忑忑。索性起床,扭亮灯,补写日记。昨天下午,我还去了市图书馆,参观乔木赠给家乡的一万多册藏书。馆方专门为他的藏书辟了一室。连书橱都是从他北京的家里运来。卷帙浩繁的马列著作。装帧神气的中外大百科全书。鲁迅全集。各种文学、社会科学期刊。让我摩挲再三、不忍释手的,是作者的签名赠送本。就中有梅兰芳、巴金、冰心,还有臧克家、季羡林、王蒙。岁月不居,流光不老,飞鸿雪泥转瞬间凝为永恒,芬芳的将长葆其芬芳。馆前左侧,矗立着乔木的汉白玉胸像。纷飞大雪之中,钱玉新局长,沈彦教授,还有我,眯缝着眼摄影留念。
胡乔木生平陈列馆
谢天谢地,下半夜停了雪。早晨,又迎来了一轮大太阳。钱局通知午后出发,趁这半日空闲,我取出有关二乔的资料,随便翻。有人奇怪我为什么对二乔感兴趣。我也奇怪他们为什么对二乔不感兴趣。有件事这里必须预作交代:我虽然也是盐城籍,与二乔同乡,但我和他俩,八竿子挨不着。于乔木,仅在人丛中见过两次尊容,一次是观看江苏淮剧团演出《奇婚记》,在王府井吉祥戏院,一次是出席首都振兴盐城咨询委员会的例会,在长安街上的某处招待所;与冠华,始终缘悭一面。
胡乔木故居陈列室(颜世贵摄影)
到了村前,反而又不敢相信,这就是张本庄?这就是一代理论大家乔木的故乡?一簇又一簇的平房,松散而疲沓,低矮而敝旧,齐来撞我的眼珠,撞得生疼。恍若仍穿行在往昔的阴影,左瞅,右瞅,哪户也不像名门望族乔木祖上的故居。喏,这边,那边,几个闻讯拢来的乡人,争着为我指点,说,当年,这一片都是乔木他们家的,房子很大,也很多,这么多年过去了,后人又都离开,自然难得保留,统统拆了,只剩下两间柴禾房,和连着的一个小天井,如今挂了块牌子,算作故居。烦乡人指引,找到那个天井。院子的一角,七横八竖地摆了一堆断碑,拂去尘土,仔细辨认,有民国立的,有清朝立的,内容不外贞孝节义,碑主都是乔木的先人。柴禾房上了锁,找人打开。迎面墙上,挂着一幅乔木的油画像,色彩灰暗,画技拙劣,感觉上是这样。室内摆了几排旧桌凳,是供村里幼儿园的孩子上课用的。此外,便一无所有。没有说明,没有图片,没有任何能勾起回忆、激发联想的陈列。无所瞻仰往往也意味着无限丰富,目无所障,心无所碍。然而,目光偏偏又停滞,在屋角的蛛网,在地面的残砖。思维偏偏又窘迫,为了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沉默也不是,发问也不是。绝没想到,做梦也不会想到。早知如此,此番又何必颠颠地跑来,千里迢迢?概念的错误,坐在书桌前空想的错误,策划的失误。但是,我并不后悔,也不着急退出。就像此刻,静静地,静静地,与乔木的画像四目相对,咀嚼渗入骨髓的人生况味。
胡乔木故居小院
说不清过了多少时候,乡人提醒说,那边,那边,靠着河码头,有一棵白果树,是乔木小时候亲手栽的,你要不要去看一看?还是有纪念意义的!长长地吁了一口气,转身出得天井,数十步外,赫然见一株老银杏,披满身晶莹的残雪,抖擞在寒风中。银杏是树中真正的乔木,耸天立地,而又脱略是非,超然物外。嘉木无言,最坚韧的生长最慷慨的绿阴最庄矜的操守,以及最默契的交流,就是无言。霎时,真想为它写一首诗。但是,拐角处的一爿(pán)商店,坏了我的兴致;那像电话亭一般宽窄,却比电话亭湫隘(jiǎoài)数倍也寒伧(chen)数倍的杂货小店!加上那位小学校长的一番直言,更让我陷入彻骨的苍凉——我一来就注意到,老房的后墙正对了一所小学,据讲就是乔木当年读书的张本小学——校长是位年轻人,一直陪同转悠。临别,上前跟我握手,激动地说:跟村里提过多次了,要他们整修整修故居。愣没人理,讲费那个劲干啥?不会有人来参观。今天,你不就来了。你有名片吗?请给我一张。我要告诉他们,谁说没有人来!
三
盐城市建湖县庆丰镇东桥村乔冠华故居
转道拜访冠华的老家。汽车七拐八拐之后,驶上一条村路。路面泥泞,而且坑洼不平。不仅仅是坑洼,两道宽窄不等的平行车辙,从这头一直连接到那头,犹如两道深沟,逼迫车肚只能贴了地面爬行。遇上两侧沟底深浅不一,车身就作大幅度倾斜,像玩杂技。这是我生平走过的最差的一段路;但这是近路,司机说。路的左侧傍着一条小河,流水潺缓而澄碧,西斜的冬日醺醺地冲波而来,溅人满眼的金芒和银芒。右侧是一望无尽的农田,柔雪欲融未融,麦苗将青未青,捂盖着、酝酿着大自然一段缠绵悱恻的爱情。偶尔见三五人家,灰墙青瓦,杂以茅舍,门前照例有几垛稻草,金字塔般庞伟,古堡般幽秘,在一闪即逝的童年的梦境。
当代人难以理喻,乔木年最后一次离家,直到年去世,在将近六十年的岁月中,再也没有踏上故乡一步。他这是怎么了?故乡难道如此不值得回首?忙,自然是理由之一,但这不应作为全盘的、绝对的借口。毛泽东日理万机,阔别三十二年照样有韶山之行。乔木若想衣锦还乡,有的是机会。譬如,他六十年代有一段长期休养,四海云游,足迹遍布杭州、长沙、大连、哈尔滨、昆明、广州,甚至奋勇登上了华山、峨眉山——就是没回苏北。也许因为他的家庭成分属地主,在历次政治斗争中埋下了难言之隐?也许还有其它什么更为深层的心理障碍?说他漠视故里,忘情桑梓,纯属误会。不管做了多大的官,乔木骨子里还是一介书生。是书生,就摆不脱书生的莼鲈之忆,故林之恋。“千古苍茫青史梦,一年迢递故乡心。”“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尤其是鸟近黄昏,人当岁暮。乔木岂能例外?种种寒梅之约、重阳之期,都交臂而错了。前尘如海。来日无多。该了的要了。该结的要结。年五月,他终于偕夫人谷羽,从北京南下,计划取道南京、扬州,转赴盐城。事情看来已板上钉钉,乡亲父老方翘首以待。车抵南京,诸事顺遂。谁知到了扬州,乔木突然发生便血,匆忙掉转车头,回南京作检查。检查结果,病在直肠,情况严重,不容疏忽。于是乎断然改变行程,回京治疗。这一去,就再也没能回去;正应了前人的浩叹:“不是不归归未得”,“断肠烟柳一丝丝”。
胡乔木与毛泽东在一起的经典瞬间
毛泽东接见乔冠华
简直是惊人的巧合,冠华也是年最后一次离开东乔庄,从此没再踏上故乡一步。那年夏天他从清华毕业,准备取道上海转赴东瀛,途中,顺便回家探亲。在盐城,冠华见到因病在家“蛰伏”的乔木。后者正和他的大哥乔冠军联手,编辑文学刊物《海霞》。是年秋天,两位老友相继远走高飞:冠华去了日本,又去了德国;乔木去了上海、杭州,又去了延安。像一朵云,飘啊飘,飘啊飘。他俩把自己交给了风,风把他俩交给满世界,就是没把他俩再送回来。说话到了年,冠华陪外宾游览扬州(注意,又是扬州!),眼看到了家门口,难免触发“越鸟南枝、池鱼故渊”之眷眷之依依。他多想回家走走——像每一个倦了的游子那样,像一切普通人那样。无奈国事纷繁,身不由己。当时,正好有一位盐城籍的女翻译,请假回家看望父母,“乔老爷”找来她,郑重交代:我也想回去,可惜走不开。你这次探家,务必多拍一些照片,带给我看看。女翻译不负所托,曲折而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冠华收到那沓照片,那沓包括他出生地和中学母校在内的照片,想必是百感丛聚、千念并袭;心头当有一支横吹的洞萧且吹开陶潜的黄花吹淌李白的月光吹炽柳永的归思。冠华最终是带着这笔相思债,不,乡思债,走完余生。他于年9月去世,从年秋天算起,漂泊在外正好历半个世纪。章含之在《故乡行》一文中透露:冠华“晚年思乡之情很浓,常常与我谈他的童年、少年、谈他的家庭、村庄。他叹息说从清华毕业后五十年未曾回家乡。”说这话的时候,应该是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站。呜呼,“白头归未得,梦里望江南。”冠华在家门口留下的余恨,不啻是前面提到的七年后乔木扬州之行的预演。
四
冠华的故居坐落在一处高墩,远远看去,颇似北方的四合院。这种高墩我很熟悉,盐阜地区历史上多洪水,居住在低洼地带的乡民,为防患未然,砌房前,每每就近取土,一箩一筐地垫高屋基。那挖过土的地方,就成了池塘,那垫高的屋基,就成了“土墩”。冠华故居的正房,一明两暗。西边一间带阁楼,是他幼年的卧室。三间正房,如今都辟作展览厅,墙上挂满他各个时期的生活照片。冠华的特点,或者说绝艺,是大笑。看过去,没有一张照片是板着面孔,无论多么庄严、庄重的场合,他都有本事咧开嘴巴,或作莞尔,或作捧腹,与乔木的拘谨、矜持,适成鲜明的对比。一位外国记者,曾把他在联合国会议上旁若无人、开怀大笑的场面摄入镜头,并因此而夺得世界新闻摄影大奖。
年10月,第26届联大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乔冠华(左一)、黄华(右一)在第26届联大上。中新社资料图
故居的后墙,据介绍,本来挨着一条河。河的北岸,有一方池塘,塘中有一个土墩,那就是冠华童年时的“小岛”。冠华父亲在上面盖了两间茅屋,屋旁栽了花,岸边植了柳,塘里养了菱藕。有四年光阴,那茅屋,就是冠华的家塾,那小岛,就是冠华的乐园。今天,这一切都已化作了漠漠平畴。站在屋后,追念“那随风飘去的岁月”(章含之语),忽然想到,也许正由于那一段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家塾生活,滋长了他刚烈而又不折不挠的叛逆。冠华而后进过四所中学,中间因为闹风潮,竟被开除三次:起初进的是亭湖中学,一年后被除名;换到淮美中学继续上初二,不久又遭斥退;家乡没书读了,就走一位母舅的门路,转到靖江准安中学,越级读高一;高一没念完,又蹈覆辙;他不气馁,再次走一位族叔的门路,转去南京钟南中学,径直读高三。六年中学,前后只读了三年,屡遭除名而又屡屡换校屡屡跳级——这份疯狂,或曰风光,除了他乔公子,我不知道还有谁?
冠华在高中最后一年踔厉风发,终于以十六岁的稚龄,考进清华大学。起先投在朱自清门下,读国文,一年后,为赢得更多的自学时间,满足自己的发展欲,又改投冯友兰、金岳霖门下,读哲学,这是他人生走向的转折点。四年大学,冠华藏锋敛锷,变得出奇的规矩和勤奋。他把自己牢牢封锁在知识的营垒,连清晨跑步,也要一手拿着纸条,一边背外文单词。课外最爱泡图书馆,并在那里结交了钱钟书。两位天才少年读书的蛮劲相似,范围有别,钟书包罗文史哲,冠华偏重于近代史,以及政治理论。冠华晚年作口述自传,说:“我主要的兴趣是利用课余时间到图书馆,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这个名词,早在中学时代我就听说了,但是马克思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到了清华以后,我有机会阅读英文的、德文原版的马克思著作。……几乎马克思的所有重要著作,我都读过,有的读了不止是一遍。”俗话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明白了冠华在清华是如何韬光韫玉,藏器待时,你便明白他后来在日本和德国的深造,以及在香港《时事晚报》岗位上的“超级爆发”,不过是水到渠成,势所必然。
乔木的中学生活,比起冠华相对平稳,尽管曾因参加街头演讲而被当局逮捕,曾因替进步学生仗义执言而与校方发生冲撞,但那都是小小的浪花一朵,转瞬即逝。跨进清华,乔木一扫既往的温良,谦恭,而日趋活跃,激烈。他报考的是物理系,后改读历史系。入学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热衷于在清华园内外成立读书会,创办工友子弟夜校,创办农民补习学校,公开传播革命思潮。乔木的头角越来越峥嵘,校长翁文灏有点吃不住劲,大一暑假前,他找来乔木,说:“清华园好比一座大戏台,生旦净末丑,各种角色都可以登台表演。要是大戏台塌了,就谁也演不成戏了。你演的戏太危险,会把戏台搞塌了。作为校长,我希望你今后不再参加此类活动。”
年4月,胡乔木与家人合影。中坐者左起:胡乔木的母亲胡夏氏和父亲胡启东。后排左起胡履新、胡穗新、胡文新、胡达新、张肃堂、胡达新夫人、胡鼎新(胡乔木)。
然而作为战士,乔木又岂能临阵撤退?这期间,恰巧共青团北平市委调他出任专职的宣传干部,他于是当机立断,离开清华园。想不到的是,乔木在新的岗位尚未来得及施展拳脚,竟因莫须有的“右倾”罪名,被停止工作,“挂”了起来。乔木刚刚失学,旋又失业,身心遭到重创,不得已,请假回老家养病。这是他生命的低谷。乔木没有彷徨,更没有消沉,而是胸怀朝阳,磨砺以须,并在盐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年后,他再度出山,考进浙江大学外语系,插班读二年级。乔木在浙大虽竭力隐蔽身份,奈何隐不住胸罗的万丈光焰,就像花果山的石猴藏不住目中的两道金光。因此,在结束大三行将跨入大四之际,到底还是被校方定为“异端”,并被褫(chǐ)夺学籍。乔木先后考进南北两所名校,都没能完成学业,未免可惜。好在天铸英才,不拘一格。乔木在大学期间受到的挫折,毋宁说磨练,恰恰为他嗣后出任毛泽东的秘书,做出了必不可少的远程铺垫。
五
乔木的名山事业在于理论。他一直活跃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是响当当、铁铮铮的“党内一枝笔”,许多彪炳史册的文献,如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由他一手整理;跨度长逾两个革命阶段的中共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是由他参与或负责起草。
冠华的千秋重彩在于外事。新中国外交史上,如果说,光前裕后的,数周恩来,光明磊落的,数陈毅,那么,光彩熠熠的,则数他乔冠华。年,联合国大会恢复我国的合法地位,毛泽东就欣然点名:“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做团长。”
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在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我曾想,假若当初毛泽东不为二人断名,就让两个“乔木”和平共处下去,生活将平添多少热闹?“南乔北乔”的绰号势必会继续下去,“大乔小乔”、“内乔外乔”、“谷乔龚乔”之类的绰号也会满天飞。
这未必不是一种大度,一种华美。
由冠华老家返回市区的途中,接京城一家刊物老总的电话,谈到进行中的这道选题,对方说:二乔生值社会转型的激烈期,一生山重水复波澜万状,一篇散文恐怕很难讲清楚;这样吧,你能不能先用一两个例子,为我勾勒一下二乔的人格特征?
我想了想,说:可以。
譬如乔木的“校勘心态”。你有没有留意到,乔木读他人的文章,读得很细,很细,细到一句话、一个词、一个标点,都不会轻易放过。举一个例:乔木读陈祖芬的《祖国高于一切》,怦然心动,于是给作者写信,表示自己的激赏。你猜他的信是如何写的?通篇赞扬的话,只有一句,就是开头说的“我很感动地读了你的《祖国高于一切》”。随即掉转笔锋,说:“作为微小的报答,我想从修辞上同你商讨几个词语的用法。”接着详细列举了他所认为的五个用词错误,诸如“拥有”后面不能接“着”,“人才”后面不宜跟“们”,建议作者再版时予以改正。不独致陈祖芬,乔木写给许多文化人的信,包括写给周扬、张光年、穆青、黄永玉,都是这个风格。这多半与经历有关。乔木走近毛泽东,接手的第一件事,就是校勘文件。毛泽东谆谆告诫:“校勘这工作要很细心。校勘又称校雠(chóu),就是要像对待仇人那样,把文章中的错误校出来。”挑错,这就是他的职业。他的敏感,他的兴趣,他的全部神经末梢,都执著在这一点,纠缠在这一点,融会在这一点。潜移而默化,积久而成习,无形中又把这种“校勘”心态,扩散到生活的其他领域。
年6月9日,胡乔木、谷羽看望钱锺书、杨绛。
冠华的人格特征,我想借他的创作立论。比起乔木,冠华无疑更属性情中人。章含之就说他:“其实你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唯一不适合你的就是政治家。你毫无掩饰地宣泄你的感情,这就是搞政治最大的忌讳。”遗憾的是他偏生选择了政治。冠华晚年,每当感情的洪流冲决堤坝,急欲择地奔泻之际,他常常驾轻就熟地活剥几句前人诗词,敷衍成打油诗。如《九·一三有感》:“月黑雁飞高,林彪夜遁逃。无需轻骑逐,大火自焚烧。”如《从上海飞巴黎》:“我辈乘机将欲行,忽闻黄浦淌歌声。长江万里深千尺,不及同仁送我情。”如《重游白云山》:“白云山上白云飞,白云山下爬乌龟;乌龟不知何处去,白云依旧笑朝晖。”这本来只是一种小家碧玉之扭捏而非大家闺秀之雍容。然而,就连这种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家胸中之块垒的杂耍之作,也难逃某些“整人专家”的狼牙棒。你在,你有所表现,你有所宣泄,这就是罪。山高雪寒,树大风烈,一至如此!灯台下多阴影。显微镜下无美人。你让他还能如何风流倜傥?你让他还能如何壮怀激烈、乾坤一掷?冠华倘若不是为政治所羁勒所击溃,以他的天赋,完全可以写出如天马之行空,独往又独来的大匠之作,大美之作。但是,他只能付之阙如。这是冠华的不幸,也是他的不争。
乔冠华与章含之在史家胡同家里
“射虎山中如昨日,骑鲸海上忽千秋。”奄忽之际,二乔都已化作前尘。乔木之为人,冷峻而严谨而拘泥而又迹近淡泊。值此身后,每有纪念他的文章发表,大抵以政界,且上层人士为多,文章的格调,也偏于严肃、恭谨与平和。冠华晚年,仕途大翻车,从云端跌落沼泽,以大笑而为人格象征的奇男子,最终只能屈身长叹,赍(jī)志而殁。这些年来,幸得夫人章含之,以一枝梨花带泪之笔,矢志不渝地为之辩诬,为之洗雪,为之招魂。——红颜中有如斯之知己,冠华九泉回眸,当应仰天笑慰。
年2月19日阳光阁
卞毓方先生近日书法习作:
长按
本文编辑:佚名
转载请注明出地址 http://www.bianyemua.com/bymjz/10494.html


